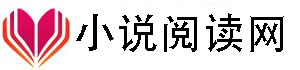110-120(5/18)
纪春山语重心长地剖白换来的却是赵明州一声善意的轻笑:“纪道长,怎么,咱们道观现在改月老祠了?你这是把我最后一个躲清静的地方也污染了啊……”
赵明州站起身来,随意正了正衣冠,纪春山也随着她的动作抬头,屋外的阳光洒进来,给女子微扬的下颌线读了一层金边。
“纪道长,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,我和般般终究是要走的。无论我们拼尽全力对这个时代做出了怎样的改变,无论我们结交了怎样生死相依的朋友亲人,我们终究……是要走的。”
“你若是真心为了朱由榔好,就别再撮合我们,这对我对他都不公平。”赵明州说完,头也不回地大踏步走了出去。
纪春山没有拦阻,只是目光在那挺得笔直的脊背上黏着了片刻,叹了口气:“油盐不进,过犹不及。”
前脚刚踏出殿门,赵明州那笃定的脚步便乱了起来,她迅速窜到庭院里,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她用手扶着一株圆柏的树干,垂着头盯着地面。热腾腾的血气充溢上头脸,被秋日的凉风一扑,让薄薄的面皮儿呈现出一种好看的绯色。
在她心目中,与其说朱由榔是一位帝王,倒不如说,他是一个温柔的影子。他陪伴在她与般般身边,从不插手,从不多话,从不找事,她让他做什么,他便做什么;般般央他说什么,他就说什么。他尽心尽力地做着她们的傀儡,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怨怼。而这样的时候多了,时间长了,连赵明州都快要忘了,朱由榔也是一个有自我意识,有独立思想的人了。
她自问穿越到这个时代之后,她没有向封建主义低头,没有压榨过任何人。可她却忘了,她真真正正奴役过的,只有朱由榔一人。
他真的还是他自己吗?还是说,他早已被迫变成了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……
一股巨大的愧疚感涌上心头,赵明州突然觉得朱由榔格外地可怜。她并不是没有感受到他对待她的与众不同,只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的温柔与退让,让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“不
同“,以至于可以任意驱使这种“不同”。
人们都说,在临死之前自己曾经的人生会如走马灯一般从脑海中掠过。赵明州是死过一次的人,她没有体会过所谓“走马灯”,但她承认人在死前尚有残存的意识,会挣扎着发出对世间的最后一次呐喊。
就像华公子会说,若能改天换地,华夏至死不渝;她会说,为了妹妹和自由,我战斗到了最后一刻……那朱由榔该说什么,我尽职尽责地过了傀儡的一生吗?
脑中混沌一片,赵明州扶着树干站直了身子,目光却僵住了。
被她目不转睛死死盯着的朱由榔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,想要换般般出来,可般般却打定了主意让朱由榔自己跟姐姐说,赵明州就这样看着朱由榔呆立在原地,面色变了数变,终于移步向她走来。
自从朝堂上风言风语乍起,朱由榔就很避嫌地减少了和赵明州单独见面的次数,即便是见面,那也是般般和明州两姐妹之间的私聊,他从不参与。
今日这一见,倒是把二人肚子里的话都掏空了,互相看了半晌,朱由榔才憋出一句:“朝堂上那些事,还请赵将军不要忧心,我……我一定能处理好。”
看着朱由榔那张欲言又止,小心翼翼的脸,赵明州的声音也不自觉地柔和下来:“没关系,我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困扰。”
她说了假话。
“你也知道,我没有存那种心。”
朱由榔轻轻抬眸,和赵明州的眼神一触,便又匆忙移开。
“北伐在即,将军的全副心思自然都专注于此,我懂得。”